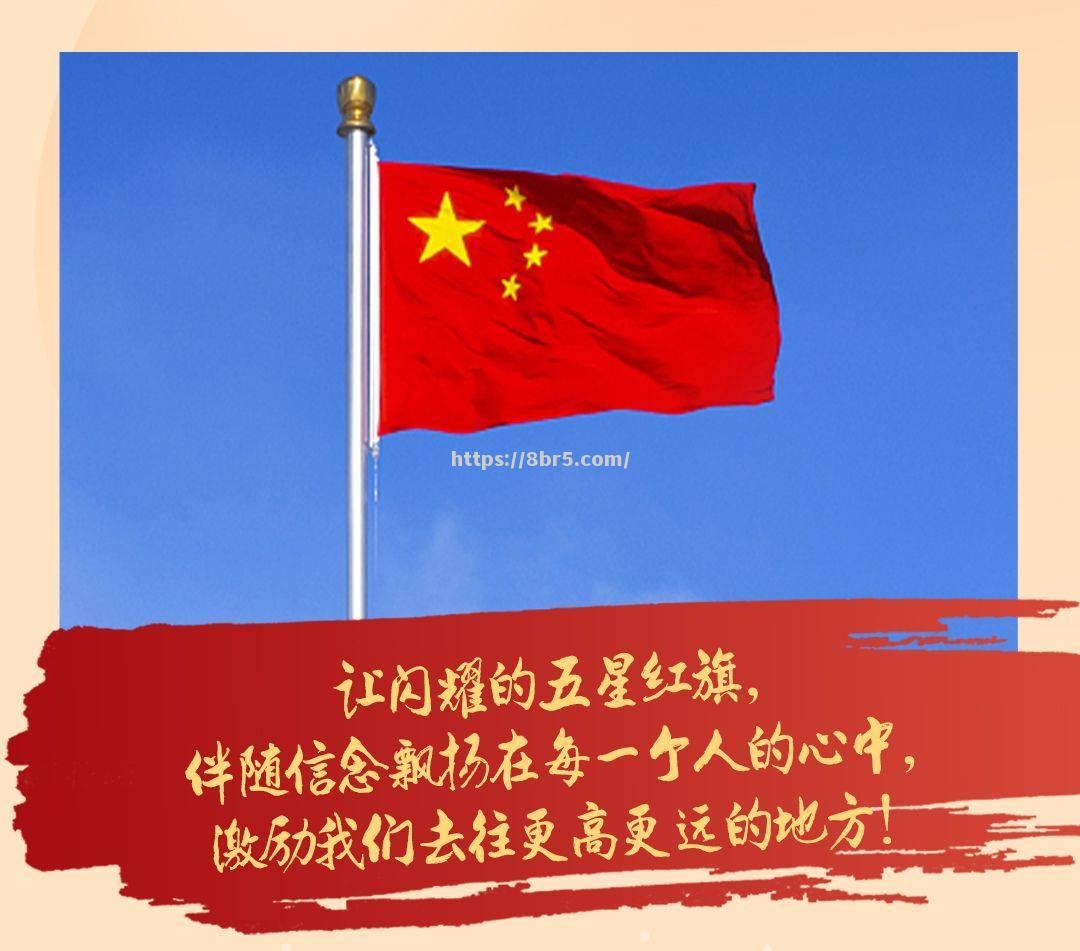桑原武夫(1904-1988)是日本著名的法国文学、文化专家摩特主场碾压甘冈,豪取三分,由于其父桑原骘藏的关系,摩特主场碾压甘冈,豪取三分他很早就得以亲炙西田几多郎、内藤湖南等硕学的謦咳。1948年出任京都大学教授,与吉川幸次郎(1904-1980)、贝塚茂树(1904-1987)等成为战后京都学派的中心人物,共同推进各种文化和研究活动的展开。
桑原这本《论语》,最初是吉川幸次郎、小川环树(1910-1993)主持的“中国诗文选”中的一册,于1974年由筑摩书房印行。1985年推出文库本,我手头这册版权页显示是1994年第9次印刷,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每年加印一次,从中大致可以推断这个小册子还是颇受欢迎的。
日本《论语》学相当发达,成果之丰硕,也许跟中国不相上下,或者,至少可以说是别具特色、不容小觑的。桑原的《论语》,就可以放在日本《论语》学的脉络里作一考察。惭愧的是,笔者在这方面素无积累,小文仅能聊尽绍介之责。
桑原并非中国学专家,他为《论语》作注,是在吉川、贝塚两人的推举下进行的。而在此之前,专长中国文学的吉川、专长中国史学的贝塚已为《论语》作过注解,分别由筑摩书房和中央公论社出版。桑原在书中也对这两位老友的解读多有引用,并加以讨论,除此之外,更频频援引江户时代的儒学大家——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——的见解,因此本书可以看作桑原与老友、与古人的唱和。当然,这里头也少不摩特主场碾压甘冈,豪取三分了中国的“古注”和“新注”。所谓“古注”,是指魏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,汇集了汉代以后学者的解读;所谓“新注”,是指南宋朱子的注,即《论语集注》。如子安宣邦所说,今人读古典,不可能绕过前人的注释,只能在与诸家的对话中,形成自己的看法。桑原自然也不例外。
实际上,桑原成长于反儒教的社会氛围中,他早年甚至没有通读过《论语》。桑原在《我与》一文中回顾了自己的《论语》经验。其中他写道,当时京都一中还保留着汉文“素读”的传统,老先生强调背诵比理解更重要。桑原清楚地记得老先生教“子曰”的读法,一般读作“シイワク”即可,但出于对孔老夫子的尊敬,必须读作“シノ・タマワク”,而不是“シ・ノタマワク”。在西风劲吹的时代风潮下,这自然招致毛头小伙子的不满。桑原也是反感孔子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。他呼吸着“大正民主”的空气,以为《论语》满是道学的臭味,一旦期末考试结束,就再也不碰这个老古董了,打算“一生绝缘”。中学时代的桑原,沉浸于夏目漱石、永井荷风的文学世界,努力摄取漱石、荷风的西欧风味,而他未曾料想这两位文豪也有深湛的儒学修养。桑原后来反省,他的汉文趣味,大概缘于这两位文学名家不知不觉间的熏陶。桑原的父亲虽是东洋史泰斗,遵循儒家的生活态度,但他并没有对儿子强行灌输儒教那一套。尽管如此,桑原在高中时听过小岛祐马讲《孟子》,且大为感动。毕竟儒教之于日本文化,犹如水中之盐,不可能稀释殆尽,所以桑原说,“儒教在不经意间如粉末一般沉积在我的体内”。
由于最初是“中国诗文选”系列丛书中的一册,限于篇幅,不可能容纳《论语》二十章。那么,如何选取内容就不得不仔细思量。为此,桑原采用了“伊藤-武内说”。伊藤仁斋(1627-1705)是德川时代富有洞察力的町人学者,他认为《论语》前十篇和后十篇性质有异,前者他称作“上论”,是正篇,后者是“下论”,具有补遗性质。武内义雄(1886-1966)是中国哲学思想史家,他在伊藤的基础上对《论语》文本作了详细的考订,其成果为《研究》一书。武内认为,在“上论”十篇中,“学而第一”和“乡党第十”是孟子以后编成的,“子罕第九”和“泰伯第八”的最后两章则相对较新。吉川指出,“上论”是即物的,“下论”则偏抽象、偏教条。日本有学者对“上论”“下论”的分法不尽赞同(如津田左右吉),但桑原基本接受了“伊藤-武内说”,也偏爱“上论”自然、素朴的行文。不过“上论”篇章仍不少,于是桑原只得进一步压缩范围,选择一些别有思想意趣、美学内涵,也更便于发挥己见的篇章。所以,该书是对《论语》前十篇部分章节的讨论,而不是全帙的解读。对此,桑原表示,未能入选的名章不在少数,而这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。

文库本通常会在卷末附一篇名家写的“解说”,大抵相当于推荐性质的导读文字。如果是译作,则由译者写一篇译后解说,除了交代翻译缘起外,一般也会对全书加以分析和评点。为桑原《论语》作解说的是日本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。在河合看来,此书有两大特点。一则,与其说它是为《论语》作注,不如说是桑原武夫与孔子两人之间的交锋;二则,它对门外汉很友好,非常有助于普通读者亲近《论语》,起到了金牌中介的作用。
的确,桑原的《论语》很有魅力,通读一过后,“读其书,想见其人”一语就自然而然浮现出来。首先,桑原强调儒教的“人间性”,而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魅力。所谓“人间性”,转换成中文,其实比较接近“人性”,总之是接地气的、实在的,而不是虚无缥缈的。比如,《论语》开篇第一章“子曰: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。有朋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,桑原认为,这三个“不亦……乎”的句型,反映出孔子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,而是以疑问的语气,温和地寻求对方的赞同(10——表页码,下同)。这一章体现出《论语》基本的言说姿态,是对话的,是温婉的,而不是高高在上、咄咄逼人的。在讨论“子曰: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。敏于事,而慎于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谓好学也已”时,桑原强调孔子的教诲从来不是抽象的,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学问(29)。此外,桑原还多次指出,孔子在音乐、诗歌方面深有造诣,且感觉灵敏,毫无疑问是可以在艺术中自得其乐的文化人,绝不是惹人厌的道学家(67)——对照上文提及的桑原中学时代对孔子的认识,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辙。更妙的是,他接着引用了伊藤仁斋的诗论,以说明诗歌的暧昧性。这则诗论充分展示了仁斋的汉文功底,姑且转录于此:“诗无形也。因物而变,为圆为方。随其所见,或悲或欢。因其所遭,一事可以通千理,一言可以达千义。故非闻一而知二者,不能尽诗之情。”
说到“人间性”,桑原特别关注《论语》中的“色”——当然是女色。譬如,“子夏曰:贤贤易色”一章,桑原对汉代的注、六朝的注都不置可否,但明确反对朱子充满道学气的解读(“贤人之贤,而易其好色之心”),并引用“子曰: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,指出真、善、美三者在孔子那里并不是对立的,而是和谐共存的。在桑原看来,热爱美人(所谓“好色”)就人的性情而言是真,就社会而言是善,就情感而言是美。(18)桑原还表示,孔子能将道德与美女置于天平的两端,说出“好德如好色”这样大胆的话,就像对待正义一样敏于美色。因此,这短短的一章为《论语》增添了无尽的光彩。(218)与此同时,桑原也直言《论语》的一个缺陷,就是谈及女性的篇幅几近于无。所以他对“子见南子”也很重视,认为孔子与女性交涉的这则故事“意味深长”。走笔至此,不禁想到一句俗语:“百善孝为先,论心不论迹,论迹寒门无孝子。万恶淫为首,论迹不论心,论心世上无完人。”假如桑原先生知道这句古话,大概率会拍案叫绝的。附带一说,桑原还提及谷崎润一郎的《麒麟》和中岛敦的《弟子》都运用了子见南子这一题材,不过中岛敦更加老到。(160-161)这可以说是读日本学者注解中国经典时的一个额外收获。
作为文学专家、评价家,桑原对《论语》中的美也格外予以关照。这里姑举两例稍作说明。一处是“子曰: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,而众星共之”。围绕这章,桑原先是引用了吉川幸次郎富有想象力的文学描写(35-36),接着提到荻生徂徕的解读。徂徕认为,“以德”是指任用贤德之才,并援引“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”以加强说服力。对此,桑原点评道:倘若接受徂徕的解释,会使北辰、众星这一意象(image)矮化为千代田城(江户城的别称)中的密室,文学之美也就随之消失了。“我宁愿抛弃那自以为是的政论,将他当作怀有爱民之心的霸主,而只品味他的文章之妙。”(37)桑原耽于美的性情于此显露无疑。
另一处是“子曰: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从我者其由与。子路闻之喜。子曰:由也好勇过我。无所取材”。对大意作了诠解后,桑原指出,本章之所以有名,与其说是由于它的内容,毋宁说是因为语言和意象的转换,节奏明快,韵律十足。先是“道不行”三字劈头而来,“不行”是抽象的,但“行”又含有行动的意味,紧接着“行”转化为“乘”。“桴”也好,“海”也罢,都是具体的、明晰的,由此前一句的悲观一扫而空。子路听闻先生之言,喜不自禁。最后却以孔子半开玩笑的口吻打趣子路落幕。情节跌宕起伏,场景活泼生动,桑原也为之兴奋,遂以古典音乐中的快板(Allegro)转为行板(Andante)为喻,指出其整体氛围是轻松愉快的。(102-103)如此潇洒的解读,与原文相得益彰,尽显桑原的当行本色。他人即使想学,恐怕也难以达到这般程度。
阅读经典的一大乐趣,就是看他人对同样的文字作出不同的诠释。坦率地说,桑原所贡献的独树一帜的解读并不是很多,不过有几则实在叫人感叹他的脑回路与众不同。其中之一是关于《论语》“学而第一”第二章的讨论。“有子曰:其为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鲜矣。不好犯上,而好作乱者,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。”对文本稍作梳理之后,桑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:有若在讲“孝弟乃仁之本”时,为什么会扯到“犯上、作乱”?在桑原看来,“学而第一”基本上是孔门的“学问论”,开篇第二章就接触到这种内容,委实说不上愉快。接着,他似乎对自问给出了自答——在乱世高举道义之旗的,以孔子为首的学问集团,在当时的权势者眼里,也许是一个隐匿着反体制志向的、危险的团体,墨家就以“儒家是反体制的”为由而大加批判。在孔子之后,才具平庸的有若想要维持这个团体的发展,于是竭力展示自己孝悌的涵养,祭起“仁是家族道德的基础”这一大纛,在政治上必定是柔顺的,而不是反体制的,以打消当权派的顾虑。(12)且不论这个分析本身是否合乎情理,桑原这个自问自答,是在常人不闻不问之处作了一番文章,单就这一点而言,是很值得称道的。另外,有若因长相酷似孔子,而被奉为孔子的化身,桑原指出在那个时代相貌里藏着难以捉摸的力量,显示出求真的学问与诡秘的巫术之间的张力。这里也反映出桑原敏锐的洞察力和奇妙的想象力。
读桑原此书,最大的欣喜来自伊藤仁斋(1627-1705)和荻生徂徕(1666-1728)两位古学派大师的注释。此前读子安宣邦《孔子的学问》时,就注意到这两人的思想能量。可是一来时隔两年,早已忘了一干二净,二来这次直接阅读日文,印象更加深刻。以下就分别挑几则,尝鼎一脔。先说伊藤仁斋。仁斋对《论语》推崇备至,誉之为“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”。本书开篇,仁斋就隆重登场,在他看来,“学而第一”首章就是一篇“小论语”,浓缩了孔子思想的菁华,荟萃了《论语》的全部精神(7)。仁斋再次亮相,且给我深刻印象的地方是他对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一章的诠解。仁斋指出,曾子这三条反省都与他人有关,这表明原始儒教的精神,不是独善的、冥想的,而是实践性的,重视人际往来的;不是哲人的自言自语,而是对话性质的;不是抽象的,而是与身体紧密相连的。(15-16)
与仁斋相比,徂徕出现的次数更多,大约是全书出镜率最高的学者。徂徕对《论语》的诠释,以政治性解读为特色。比如,“子曰:君子怀德,小人怀土。君子怀刑,小人怀惠”,这是《论语》很难通解的一章。在此直接奉上徂徕的解说。徂徕认为“君子”指统治阶层,“小人”指平民百姓。通常都是将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作道德性的解读,而徂徕这种政治性的视角,颇有片语解纷之效。倘若统治者讲道德,平民百姓就可以在故乡安居;假如统治者对犯罪活动严惩不贷,平民百姓自能从中得到实惠。(86)虽说经典阅读不存在唯一正解,但就《论语》此章而言,徂徕此说或许可以列入最优解的行列。
试再举一例。“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”,这章也是言人人殊、莫衷一是。何晏的“古注”、朱熹的“新注”都是八字连读,并未点断,而徂徕将其截为两句,提出新说,此后武内义雄、贝塚茂树都采纳此说。徂徕认为,孔子虽然很少谈“利”,偶尔涉及这一话题,往往和“命”“仁”放在一块儿谈。尽管略显曲折,但确实不失为一解。桑原认为此说“理路整然”,清代的焦循也有同样的解释,大概是受了徂徕《论语徵》的影响。(202)

值得一提的是,徂徕对《论语》的解读,经常跟朱子唱反调,不过他有时也赞成朱子的意见,然而后人读了,不免要大吃一惊。譬如,“伯牛有疾。子问之。自牗执其手。曰:亡之。命矣夫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。”这章也有几处众说纷纭的地方,且不管它。有意思的是,朱子对此作了教条式的道学解释,不曾想徂徕大表赞成,桑原立马加了一句“面白”(138)——直译是“有趣”的意思,但我想这里面还蕴藏着“大跌眼镜”这层含义。
末了,再举一例。徂徕对《论语》最具颠覆性的一个解释,或许是对“宰予昼寝”的判断。一般将“昼寝”理解为“大白天睡觉”,但课堂上打瞌睡怎么会惹得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夫子那么恼怒,以致说出“朽木不可雕也。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”之类的重话,终究有悖常情。由此疑问出发,徂徕根据《礼记》檀弓篇,将“昼寝”解作“昼处于寝,盖有不可言者焉”,但怎么个“不可言”法,还是一团浆糊,未得分明。而桑原径自解释为,大白天调戏女性,因此孔子大发雷霆。(107)这么解释,道理是讲通了,但“昼寝”究竟是怎么回事,似乎仍是一个谜题。而且,这里涉及经典诠释的再诠释问题——徂徕只是隐晦地说“盖有不可言者焉”,是否就是桑原解释的那样,愚钝如我,总感觉要打个问号。
传世经典里肯定有不少地方是聚讼不已的,学者或列出几种代表性的意见,或在此基础上自出机杼,是古典今注的常见套路,也是必备技巧。桑原《论语》就举了日本学者很多独到的见解,这一方面对我们理解《论语》是很有启发的,另一方面也增添了阅读的乐趣。就宰予昼寝这个问题,贝塚茂树贡献了他的奇思异想。据贝塚分析,宰予后来成为与孔门对峙的墨家一派的实用主义者的先驱(107)。思想分歧固然可以构成孔子大骂宰予的一个背景,但“昼寝”依然难解。不管怎么说,贝塚这条解释是另辟蹊径,而不是“重蹈覆辙”。另外,像“父在观其志,父没观其行”,“其”字的读法是理解的关键。“其”是指父亲,还是指孩子?一般都解读为儿子。孔安国、朱熹、仁斋、徂徕、吉川、贝塚,率皆如此。然而,桑原在此处却倾向于采用钱大昕及简野道明、木村英一的解说,认为“其”指父亲,理解起来更自然。(24-25)再如,“子曰:人之过也,各于其党。观过,斯知仁矣”。围绕“党”字,桑原举了朱子的宋学式的、基于客观立场的解读,仁斋的日本式解读,以及徂徕政治性的解读,最后表示自己无力作最终判决,读者可各取所好。(80-82)这种例子甚多,恕不一一。
读桑原《论语》,另一个乐趣在于寻觅书中流露的个人偏好和个人史。对学术史、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,恐怕多少都有一探名人“八卦”(说得好听一些,或可称作学林掌故)的心态。哪怕片言只语,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探求的线索。比如桑原提及曾跟晚年的狩野直喜闲谈,狩野对宋儒的道学气大加揶揄(18)。再如,讨论“伯牛有疾”时,桑原回想起他曾探望命在旦夕的高桥和巳(1931-1971)。高桥是吉川幸次郎的高足,那么也是桑原的学生辈,后来则同在京大任教,却因罹患癌症而英年早逝。在高桥的告别仪式上,桑原提到了孔子和冉伯牛的故事,并表示这是他铭感至深的一章(139-140)。书中还提到高桥最喜欢《论语》中的某一章(169),而桑原最喜欢“达巷党人曰”一章,因为“执御乎,执射乎”显露出孔子的幽默,书中作了很有画面感的解读(204-205),不由得也让人心生欢喜。像这种透露个人性情和历史讯息的解读,无疑是弥足珍贵的。
能够体现该书时代性的一个议题是“中国历史的停滞性”。书中至少有两处涉及这个话题。一是“君子不器”,桑原引用韦伯的见解,认为“不器”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原因(51)。一是“信而好古”,桑原以为尚古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有密切的关系(166-167)。另一个暴露其时代性的表述是“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封锁安定社会”(118),而小熊英二于1995年出版了《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:“日本人”自画像的系谱》,其时桑原已驾鹤西行。
《论语》对日本社会的影响,自然也是日本学者关心的。书中明确提到这个问题的,似乎有三处。一是,桑原认为,孔子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”的观点可能给日本国民性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所谓文明社会,就应该做到内容真实与形式优美相协调,因而真相就应该堂堂正正公之于世,而奠立在素朴实在论基础上的日本社会,在人际关系方面就未能达到洒脱、协和的目标。(14)二是,“食不语,寝不言”,桑原认为这章影响了日本人的饮食起居。据桑原观察,由于日本人总是默默进食,很少在餐桌上高谈阔论,所以他们在法国时经常被询问:你牙疼吗?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?(229-230)三是,桑原指出,曾子的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对日本武士有着巨大的影响,并以加藤清正为例作了说明。据说前田利家(1539-1599)曾对加藤清正(1562-1611)讲过“曾子曰:可以托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,君子人也”这一章,清正当时并不明白此中意涵,到了晚年学习《论语》时才幡然有悟。因此,在庆长十六年(1611)三月,当德川家康(1542-1616)邀请丰臣秀赖到京都二条城会面时,清正怀揣着太阁(即丰臣秀吉,1537-1598)送给他的短刀,护卫秀赖,会见结束后,在安全返回大阪的船上,清正感到自己有机会报答太阁之恩于万一,不由得潸然泪下。(192)
对桑原来说,加藤清正的故事,大概就相当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“物语”。短短几句话,却蕴含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刀光剑影、聚散离合。可是,对于我这样的门外汉,只有利用电脑检索,才能略微了解这背后的历史风云。这样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,比如犬公方(26-27),比如石田三成(188),在Google的过程中学习日本的历史与文化,也是桑原《论语》带给我的最大的精神享受。